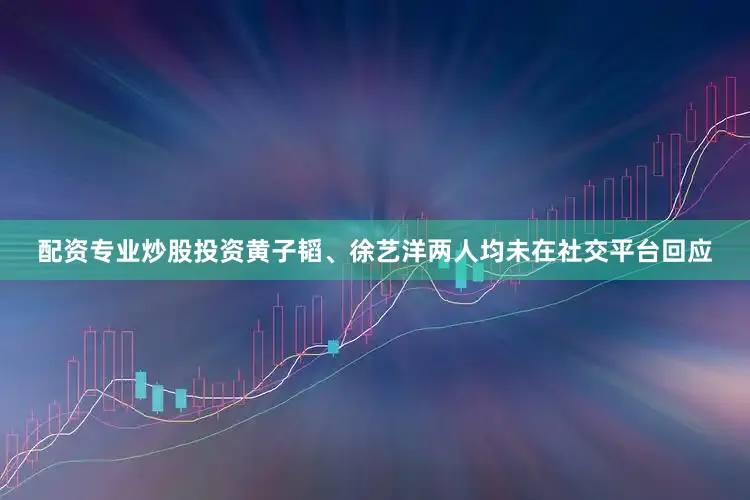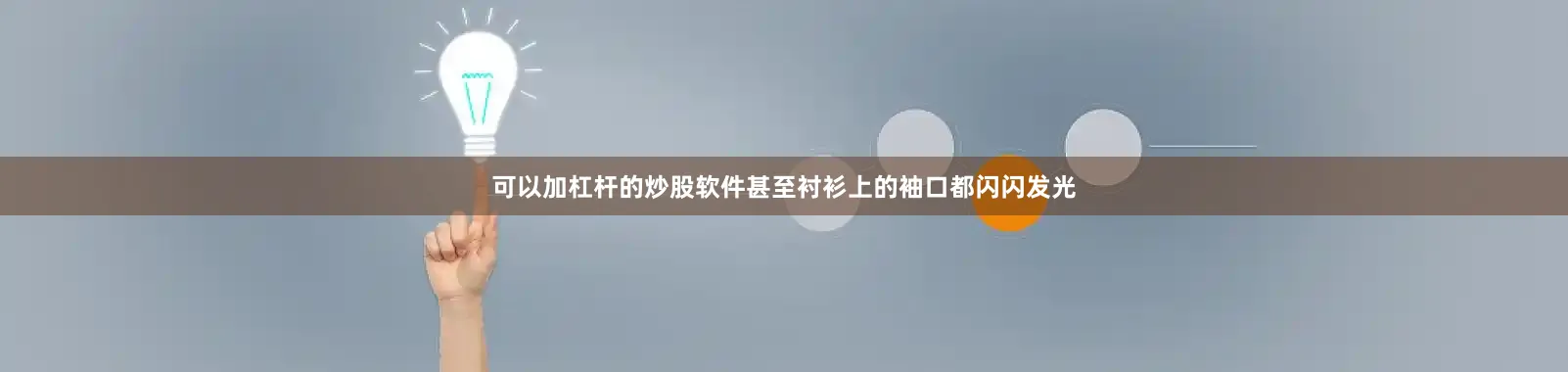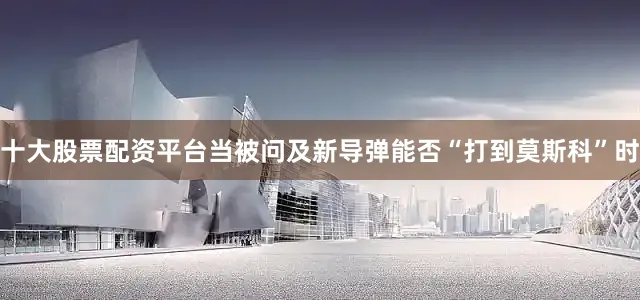我一般不会专门写本草,除非是忍不住。
威灵仙,究竟有什么魔力,让我单独开一篇给它呢?
答案在清末民初的医家张锡纯的书里可以找到。
不少人都知道张锡纯善用威灵仙,因此每每说起这味药都会首先想到他。但估计大家都未注意到,通过张锡纯笔下的威灵仙,可以发现医理被阉割了。
嗯,这就是我忍不住码字的主要原因。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对威灵仙的【主治】功能用了三句话来总结:
“诸风,宣通五脏,去腹内冷滞,心膈痰水,久积癥瘕,痃癖气块,膀胱宿脓恶水,腰膝冷疼,疗折伤。久服无有温疫疟(《开宝》)。推新旧积滞,消胸中痰唾,散皮肤大肠风邪(李杲)。”
对以上这段文字内容,我们大概只能get到其中的“风”字,然后,就没有然后了。
为什么理解不了其它文字内容?
还有,将威灵仙视为风药难道错了么?
先来回答第二个问题。
没错。威灵仙确实是个风药。
用李东垣的语言体系来转译,可以称为“升阳”药;再用本号“两线”语言来转译,也可以称为直接助力卫气线用药,也在早期“达表药”的范畴里。
作为“风药”,能治“风湿痹痛”,这是肯定的,也是目前《中药学》里列在第一位的功能。
朱丹溪有个著名的“上中下痛风方”,开头一味就是威灵仙。“威灵仙三钱、南星一两、苔芎二两、白芷五钱、桃仁五钱、桂枝三钱、防己半钱、苍术二两、黄柏二两酒浸炒、红花一钱半、羌活三钱、神曲一两炒、草龙胆五分”。
威灵仙的这一功能沿用至今,或者,更为确切地说,这是威灵仙唯一保留至今的功能。尽管大家都知道它能“治骨鲠”,但现在应该也都不会去尝试。
但在“风湿痹痛”里起到祛风作用,仅仅只是“风药”功能的一部分。
也就是说,即便我们现在只认识威灵仙作为风药的功能,也还是不完整的。
张子和(1156-1228)的《儒门事亲》里,有一个治小儿“疮疹黑陷”的简方,“铁脚威灵仙一钱炒末、脑子一分,上为末,用温水调下服之。取下疮痂为效”。
再往前一点儿,陈无择(1131-1189)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里,也有一个简方“仙灵散”,“治斑疮入眼,仙灵脾、威灵仙,各等分上为末。每服二钱,食后米汤调下”。
若是理解不了什么叫做“斑疮入眼”的话,可以来看看朱丹溪(1281-1358)对此方的衍用:“痘后生翳数服效,用威灵仙、仙灵脾等分,洗净,不见火与日,为细末。每服随时,宜第三次米泔下”。
可见,陈无择与朱丹溪俩人对威灵仙的运用,皆同于张子和用来急救小儿疮疹黑陷,都是利用了威灵仙所具有的升阳/达表的能力。
在痘疮斑疹的整个透发过程中,或是因为感受外邪,或是因为用药太过寒凉等原因,导致病人一度出现气机下陷,即较为严重的卫气稽留。气不达则疮疹不达,情势危急,此时古人会用威灵仙来升阳,助力气机恢复外达。
了解至此,才能算是接近了威灵仙作为风药的基本功用。
但,即便补充了“升阳”的部分,我们还是无法领会李时珍笔下威灵仙的“主治”啊,这不还是只get到了“风”么?
李时珍在主治里提到了李东垣对威灵仙的评价,因而我检索东垣著作,发现除了《东垣试效方》里简要概括了威灵仙的功效外,“威灵仙苦温,主诸风湿冷,宣通五脏,去腹内癖滞,腰膝冷痛”,东垣本人并没有给出过包含威灵仙的方子。只在《医学发明》里有一个“除湿丹”包含威灵仙,但那是个古方,并不是东垣自拟方。
综合李时珍所引用的东垣语“推新旧积滞,消胸中痰唾,散皮肤大肠风邪”以及《东垣试效方》里的“主诸风湿冷,宣通五脏,去腹内癖滞,腰膝冷痛”,我们还是只能get到其中的“风”。
至于,“推新旧积滞”,“消胸中痰唾”,“去腹内癖滞”,到底是怎么个“推”法,怎么个“消”法,怎么个“去”法,一概不知。不用去查你手边的《中药学》,里面没有。
无论是李时珍自己总结的主治,还是李东垣对威灵仙的评价,我们可以看到,威灵仙远远不限于我们现在认知里的“风药”,而是具有非常明确而强大的去除各种实邪的能力,如恶水、痰湿、积癖、癥瘕、瘀血…等等。
但你以前知道么?
好,即便你以前就有所耳闻,那你知道威灵仙的这些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么?具体怎么用?
我第一次领略到威灵仙不同于刻板印象中的风药,是在阅读孙一奎(1522-1619,字文垣)的医案过程中。
文垣用威灵仙的频率之高大概是古人里算得上名列前茅的了,其中大多案例的用法对我们来说比较常规,但有俩案的用法非常特别,我咋阅读当时就曾叹为观止。
一案是病人因毒结经络致腰胯剧痛,文垣等到了开春后,先是用了张子和的煨肾散(猪腰+甘遂),令其大泻数次,之后借用了朱丹溪的法子(丹溪原法为“威灵仙为细末,每服二钱,猪腰子一只,批开,掺药在内,湿纸煨熟,五更细嚼,热酒下”),又泻了一两次,病根尽拔,再行调理善后;
另一案是病人久服温补下元之药,又受风湿外寒,以致全身多处骨节红肿疼痛,卧床不起三年。文垣断为“湿热痰火被寒气凝滞固涩经络”,借鉴了唐代崔元亮的《海上经验方》(后文详说),与化湿活血通行经络的汤药间隔服用。使得病人每隔几天就通下稠粘痰积,直至消尽为止。而后再转用养血通络健脾化痰的缓法,令病人在半年之后恢复肌肉与行走。
我一边读一边自问:为什么以前从来不知道,威灵仙的强大竟然是这么体现出来的?为什么从来没有读到过有人强调说,威灵仙的正确使用法子是:
制成末,或,研末制成丸。
就在码字前我还翻阅了手头两本近年来出版的本草书,《临证本草》与《本草致用》,不出所料,都没写。
难不成是孙文垣自己独创的?
显然不是,刚才已经说了,他这俩案都借鉴了前人法。
看来当代本草书是指望不上了,于是我验证性地翻阅了清初的《本草求真》,作者黄宫绣还曾经是乾隆时期的御医。
为什么要说验证呢?因为本号常说医理最严重的降维/阉割,发生在明末清初。
李时珍(1518-1593)与孙文垣(1522-1619)都处于明中期,稍偏晚期,俩人对于威灵仙的认识,从上文的内容来看确实也是大抵趋同。
而我想要验证的《本草求真》果不其然,前人对威灵仙的主要认识在里面已经完全消失了,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。
于是我细细读了《本草纲目》对威灵仙的介绍,读着读着感觉像是在读另一个世界的本草书。也对,从医理角度而言,毕竟是另一个时空的事儿了。
通过李时珍的记载发现,原来,威灵仙的正确用法,研末与制丸,是至少从唐代就开始的。
而且,与后世区别最大的地方在于,古人都明确强调了服用后的结果:
取利。
“《千金方》,腰脚诸痛。用威灵仙末,空心温酒服一钱。逐日以微利为度”;
“《经验方》,肾脏风壅,腰膝沉重。威灵仙末,蜜丸梧子大。温酒服八十丸。平明微利恶物,如青脓胶,即是风毒积滞。如未利,夜再服一百丸。取下后,食粥补之。一月仍常服温补药”;
“《集简方》,筋骨毒痛,因患杨梅疮,服轻粉毒药,年久不愈者。威灵仙三斤,水酒十瓶,封煮一炷香。出火毒。逐日饮之,以愈为度”。
除了取利,也有取汗出与取吐痰等。
如此也就解答了我上文的几连问,到底是怎么个“推”法,怎么个“消”法,怎么个“去”法,原来古人都给了出路。
接着我继续追溯,发现李时珍对威灵仙的绝大多数介绍内容,都来自于北宋的《证类本草》,就是那本我国现存最早的且最完整的本草书,由唐慎微(约1050-1120)约撰于北宋绍圣四年至大观二年(1097-1108)。
李时珍写的那段主治,除了附加的东垣语录外,都是《证类本草》的原话。
唐宋两代对威灵仙的理解与运用,比如《唐本草》、《千金方》、《经验方》、《集验方》、孙兆用方,等等,李时珍皆原封不动照搬自《证类本草》。
而唐宋对威灵仙的作用认识最深刻的,则是崔元亮的《海上经验方》。
唐慎微引用了崔氏对于威灵仙的大段功效介绍,李时珍大概是因为篇幅关系,进行了适当的缩写。当你逐字完整地读完崔氏文字之后,就会对那一句简明扼要的主治“诸风,宣通五脏,去腹内冷滞,心膈痰水,久积癥瘕,痃癖气块,膀胱宿脓恶水,腰膝冷疼,疗折伤”,产生更为形象具体的认识。
文垣用威灵仙下经络瘀积的第二案,借鉴的正是崔氏法:
“威灵仙味洗焙为末,以好酒和令微湿,入在竹筒内,牢塞口,九蒸九曝。如干,添酒重洒之,以白蜜和为丸如桐子大,每服二十至三十丸,汤酒下”。——《证类本草》
不过文垣还进行了适当的活用:
“以新取威灵仙一斤,装新竹筒中,入烧酒二斤,塞筒口,刮去筒外青皮,重汤煮三炷官香为度,取出威灵仙晒干为末,用竹沥打糊为丸,梧桐子大,每早晚酒送下一钱,一日服二次”——《孙文垣医案》
崔氏法是将威灵仙与酒,塞进竹筒里蒸晒,而后将酒浸的威灵仙研末为丸。
但文垣制丸时,还更加了竹沥。
在《本草纲目》里李时珍收录了古人用威灵仙结合半夏皂角等,去除停痰的经验方,共三条,内容彼此相似:
“停痰宿饮喘咳呕逆,全不入食。威灵仙焙,半夏姜汁浸,焙为末,用皂角水熬膏,丸绿豆大。每服七丸至十丸,姜汤下,一日三服,一月为验。忌茶、面”;
“停痰宿饮,喘咳呕逆,同半夏、皂角水丸”;
“停痰宿饮,大肠冷积,为末,皂角熬膏丸服。或加半夏”。
之所以说文垣活用了古人法,不仅是因其在崔氏法上更加竹沥,还在于他将古人用的半夏皂角,给改成了竹沥。因为他面对的病人,更偏于痰热,热象较重。
我们现在知道了文垣对威灵仙的用法,是早在唐宋时期就常用的主用的,那么,从宋代到文垣之间,是否还有人用过?
肯定有。至少朱丹溪就是其中一位。
除了文垣案一里借鉴的“威灵仙末+猪腰”法之外,丹溪还有治痛风以汤药送服威灵仙粉末法,以及治小儿龟胸方,“苍术、黄柏酒炒、芍药酒炒、陈皮、防风、山楂、威灵仙、当归,为末,炼蜜丸。食后,温水下。又利后,加生地黄”。
龟胸,是因风痰停饮聚积于胸膈,或再加外感风邪,致肺气阻滞,痰邪重壅胸膈所致。丹溪对此用威灵仙,研末制丸,并补充说明服后会取利,由此除下痰积。
读到这里,可能有读者发现了,威灵仙有通下的能力。
张锡纯不就有用来通腑么?为什么本文一开始会说,张锡纯所写的威灵仙是被阉割的医理呢?
让我们先来看下张锡纯是怎么写的:
“一日,见(刘肃亭)先生治一伤寒,热入阳明大便燥结证,从前医者,投以大承气汤两剂不下,继延先生治之,单用威灵仙三钱,煎汤服后大便通下,病亦遂愈。愚疑而问曰:威灵仙虽能通利二便,以较硝、黄攻下之力实远不如,乃从前服大承气汤两剂大便不下,何先生只用威灵仙三钱而大便即下乎?答曰:其中原有妙理,乃前后所用之药相借以成功也。盖其从前所服之大承气汤两剂,犹在腹中,因其脏腑之气化偶滞,药力亦随之停顿,借威灵仙走窜之力以触发之,则硝、黄力之停顿者,可陡呈其开通攻决之本性,是以大便遂通下也。是威灵仙之于硝、黄,犹如枪炮家导火之线也。愚闻如此妙论,顿觉心地开通,大有会悟,后有仿此医案之时,亦随手奏效。因并录之于下,由此知医学虽贵自悟,亦必启发之有自也。”
首先感谢张锡纯记录下来,因为此案非常经典,我记得本号去年有篇文章里就引用过,参《与前医“合力”通的便~》。
从以上文字内容来看,张锡纯认为威灵仙有开通脏腑之气滞的作用。
这难道错了么?
问题就在这里。
刘老紧接着大承气汤用威灵仙三钱而取通下,我们若是将前后手法整合起来,那么威灵仙在这里的作用,就比较接近于李东垣在通幽汤里所用的升麻了。
通幽汤里加升麻,仍然是东垣“以升治升”的经典手法。用东垣的语言来说,升麻是为了令阳明经气不致遏绝的。用本号的“两线”语言来说,升麻是为了助力卫气线的,升阳以降阴火。
也就是说,在明末清初以前,古人将“经络”与“脏腑”是分开来说的。
再来看文垣俩案,也是明确说明了疾病在经络层面。如“余毒尚伏经络”、“病不在肠胃,而在经络筋骨间,徒泻肠胃无益”、“天令寒极,经络凝涩”、“足下之疾在经络”、“湿热痰火被寒气凝滞固涩经络”、“先驱逐经络中凝滞”…等等。
所以你看,孙文垣在第一案里先用的戴人方煨肾散/猪肾散,其中所用的甘遂一味,正是用来“通经”的。戴人还专门有个以甘遂为主药的“通经散”(陈皮、当归、甘遂)。
我以前很懵懂,看戴人每次用通经散,病人常常是二便俱出,就会想这明明是通腑啊,为什么取名叫“通经”呢?
去年介绍过元代医家项彦章的医案,其中有一位病人患胁痛,前医们屡用温热,致病情更甚。项彦章说你们治错了,病在肾经经络中,应该以下法利之。
我们知道肾经贯肝入肺,因而项彦章认为是此证是肾经之邪“上薄于胁”,所导致的胁痛。
于是他用含全蝎巴豆的神保丸(《脾胃论》方),得病人通下黑溲,胁痛即止。
既然是肾经经脉之邪,那么其出路自然首先就是小便了,所以小便通下了黑色尿液。
类似这样的明末以前的医案读多了以后才渐渐明白,戴人之所以取名“通经散”,是因为他要通行的层次就在经络,而不是脏腑。尽管经络之邪还是会经常转入胃肠,而从大便出来,也就成了戴人笔下“二便俱下”的效果了。
正因为是为了通行经络的,所以戴人常用通经散来治疗经络层面的疼痛。
在腰痛一门中,戴人先是批判了当时医者们总是径用温热或温补,而不管虚实,也不管病邪在什么层面,而后连举了他治疗的数例。
其中有一位病人腰痛一年多不愈,戴人见其证实,先以通经散令其通下下五六次,而后转用以食疗为主的补法,用上了杜仲与无比山药丸。整个治疗过程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,病人就痊愈了。该案在我去年介绍戴人生平的文章里出现过,参《生前身后都不被喜的张子和》。
戴人的先通下后用补的治法,正是唐慎微(李时珍转载)所记录的古人用法:
“治肾脏风壅积,腰膝沉重,威灵仙末,蜜和丸桐子大。初服温酒下八十丸。平明微利恶物,如青浓胶,即是风毒积滞也。如未利,夜再服百丸。取下后,吃粥药补之。月仍常服温补药”。
只不过,戴人用的是甘遂,唐慎微记载的是威灵仙。
两者功效类似,但有轻重缓急之别。
所以,文垣第一案先是用了戴人法,甘遂+猪腰子,接着改成了丹溪法,威灵仙+猪腰子。后者虽较前者为缓,却也还是通下了一两次。
我们可以看到,从唐宋一路到明末之前,古人都是非常严格区分经络与脏腑的。也只有在这样医理认知的基础上,才可能诞生与存续对于“两线”的认知。因为该外达的外达,指的就是经络层(表位/阳位);该降行的降行,指的就是脏腑层面(里位/阴位)。
反过来说,张锡纯将威灵仙解读为通行脏腑滞气,表面看起来是误将经络说成脏腑,实际上是因为已经根本不具备区分两者的基本认知了。
与此同时,“两线”的认知也早已随着表里阴阳的不分,消失在医理世界中了,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…
我们古人有许多成语,如“一叶知秋”、“见微知著”、“管中窥豹”、“以小见大”、“可见一斑”等等,都可以用来形容,通过一件细微的小事儿,就能看到其背后整个局势的发展趋势。
威灵仙,之于“两线”,就是这么一片令人“知秋”的“落叶”。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免费配资炒股入,配资专业网上炒股,十大股票配资平台排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